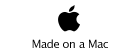蘇仲卿教授部落格
2013

引言
台灣的盛夏是陽曆七、八月,其中八月大部分是陰曆七月(鬼月)的範圍。小時候,長輩會提神,少出外曬太陽,多喝茶水以免中暑。鬼月的中元普渡活動,在日治時代亦是每年盛大舉行的民俗活動,與日人于陽曆七月十五日或八月十五日舉行的「盂蘭盆」掃墓活動並存。
每年進入七月就會想起于1937年發生的蘆溝橋七七事變,因為事變發生之時,筆者已經粗備看日文報紙能力的公學校三年級生,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已有所形成。今年為七七事變舉行的紀念活動,受到報刊讀者的許多批評;又教育部高中歷史課本審查委員會所定,有關日本統治時期的記載方式,有「日治」與「日據」的論爭發生。這兩件事的實質內容都以台、中、日之近代史觀,以及台灣漢人之歷史定位為爭論點。
七月中旬叫做「蘇力」的颱風襲台,帶來山地土石流與台北市許多街道樹翻倒的災害,但是,可能是蘇力的危害規模不如已往大颱風,有上面歷史觀論爭之外,有一位將要退伍而已經考上成大研究所的陸軍下士洪仲丘先生,因軍中行政管理不當,遭遇到不符合行政程序的禁閉處罰而中暑死亡的事件,同時成為媒體連日注目的大新聞。
我國法定服兵役為男性國民的義務。近半世紀擔任大學教師的筆者,每年七月都有男性畢業生入伍,亦有役畢退伍者繼續學業或就業,似乎造成視服兵役為教育一環的觀念。但是,洪下士之命案發生之後不出兩星期,依據媒體的報導,不能視該事件為「教育管教」之不當而有被「他殺」的嫌疑,並且,對軍方調查處理的不滿,導致八月三日洪君告別式之日,有報刊估計25萬民眾集會於總統府前廣場抗議軍方處理之不透明,並且發展到立法院修法,迅速通過非戰時不適用「軍審法」的法案。
筆者于1928年生於台灣,1946年入學臺大,初等與中等教育都是在台灣日式學校所受。所以,上面所說事件,讓筆者憶起許多往事與感觸。老年人的近代史觀,對於有臨場的直接體驗事件,可能與只有資料知識者有所不同。筆者于1935年4月入學九份公學校到1999年2月從臺大退休,未曾離開過學校,所以,以下所寫的回憶與感觸,皆為於教育場所所得。
日治與日據的爭議無意義
人一生的體驗際遇,構成個人的歷史記憶。筆者幼少年期生活於日治年代,且家有台灣換朝代的1895年,已經23歲而結婚生子的老祖母,她于1957年85歲過世之前,講了不少滿清末期的台灣農村情況。筆者雖然不能據以發表「歷史研究」式高論,覺得依據口傳與思考所形成的歷史觀,或可提出做為參考。
滿清治下的台灣,沒有報紙或其他媒體傳播消息,鄉下農民只有口傳故事與親身體驗的記憶可流傳。祖母描述她的「祖厝」有城堡式建築規劃,並必要自備槍砲自衛搶匪的侵襲,可見治安很不好。守衛祖母娘家農莊的砲手是一位「阿妗」,顯示必要集合近親人力才能構成有自衛能力的集團。我相信,馬關條約之後,日本派兵前來「領台」時,有不少義勇兵起來抗日,是因為民間有為「抗匪」的武器之故。對沒有被號召當義勇兵的農民而言,感謝終止長年土匪之害而「達成治安,可安居樂業」的「日治」是當然,因而以「日據」表達的政治立場,優先於「日治」帶來的實益,不可能存在於活過滿清朝代的農民意識中。
流傳於台灣民眾的、李鴻章在簽馬關條約時對台灣所下「評語」,有中日兩種版本;則對慈禧太后所呈的「台灣山不清,水不秀,鳥不語,花不香,男無情,女無義,瘴癘之地,棄之不足惜」,以及對和約談判對手伊藤博文所說的「台灣不可根絕之害有四:鴉片、匪賊、瘴氣、生蕃(原住民)」;沒有講出來的話是「如此麻煩之地你要嗎?」。雖然是傳說,有此傳說也夠傷台灣人之心,現代歷史學家不要忽視。
治安問題獲得解決之外,祖母稱道的有日本官員的清廉與公共衛生的改進。光復之後,聽了沒有紅包辦不了公事的新聞時,祖母所發「又回到衙門八字開,無錢免進來的年代」的嘆息,意味着大陸政權派到台灣的官,基本上都會貪瀆,還很清楚留在記憶中。又從台北市的故老聽過,日本領台後不久,台北市發生鼠疫,經過日人嚴密的處理而根絕。筆者幼時種痘之外,沒有被打過傷寒、霍亂等流行病預防針的記憶,亦可視公共衛生的改進吧。
聽說,日人來了之後有兩年間,可選擇留台或「回唐山」。對於墾地開田並且必要有自衛能力,才能保護辛苦所得的農民來說,棄地回唐山是不可想像的選擇,不得不留台當「皇民」,應該不是不可原諒的罪過。
總而言之,不管動機或源由如何,日本領台而以殖民地「統治」台灣五十年是歷史上不爭的事實。其間,不管目的如何,其行政措施與各項投資,帶來滿清時代沒有的和平亦是事實。因此,對於老一輩的台灣人,依據否定殖民地的合法性而說「日據」,或依據歷史事實而說「日治」都無所謂,因為日人的確將台灣當作日本領土的一部份而「治理」過。
日本統治政策與日本人個人的行為必要分辨
二戰結束的1945年,筆者已在接受日制中等教育的後段,對於日本統治台灣的所作所為,透過十多年的在學學習與觀察,已形成個人相當明確的「歷史觀」。講起相對日人,台人受到同職不同待遇的歧視,或高職位皆由日人佔住等不平等待遇,入殖者佔優勢,是日治時代與光復後有一段很長時間都是一樣,因為日人以武力為後盾,將一群官商人物帶進台灣接管,與光復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行政與處置產業情況類似。
筆者有一位財金專長的朋友說,日人在台五十年的投資,還沒有到回收利益的階段就離開台灣。筆者不知道他所做估算的資料來源,但是,依據1950年代執行的「耕者有其田」農地改革政策,政府給地主的農地代價,七成以「實物債券」,三成以四家日產公司(水泥、農林、紙業、工礦)的股票而達成一事,就可以理解他所說應該正確。
另外,假如沒有日人留下交通、電信、電力、水利等工程建設,戶政、教育、醫療、公共衛生等民政措施與制度,以及各項生產業等基礎建設,相信,大陸撤退後的台灣建設必更艱苦。有人懷念使用一百年還在發生效用的烏山頭水庫建造人「八田與一」」而受到批評,筆者認為胸懷不必如此狹窄。
當年的台人對日人的「皇民化」運動,是否有報刊文章所懷疑的普遍性懷念情緒存在,個人可以給明確的否定。日人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是政策;為推動,給接受者有種種優惠措施,當然會有人接受,但是,並不是為全民所歡迎。在一個社會的生活,除了大環境的約束之外,還有個人間的接觸來往。因此,對人接觸的感受,不能與針對政策的批評混淆。
日本人在台灣推動教育的普及,有說以奴化為目的。但是,知識普及而民度提升之後,「奴化」的理論與作法還會被民眾接受?更何況,日辦學校對台人灌輸的倫理道德,就是以儒教為內涵,與筆者所受家教無二致。另一方面,日人在台灣施行的「專賣」與其他限制台人經營的行業,明確是殖民政策,但是光復後照樣被國民黨政府繼承,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;光復後兩年,筆者已經有聽辨別大陸話的能力。有一天在台北火車站要搭一路公車上臺大,等車的學生民眾都排隊,車到時,忽然有兩位大陸人,一面講「你看奴性多重,乖乖排隊」而搶先上車。這等國家體制更換年代,文化的衝擊與人民所不願「殖民政策」的遺留,是要記憶或要忘記?
筆者懷念日治時代所受的教育,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紮根與體育。相信能活到快滿85歲,還可以維持不錯的生活品質,以電腦打字寫文章,應該與我所受的中學體育有關,是瞭解「洪案」發生經過之後,興起寫本文的動機之一。
但是,筆者深恨日人極端歧視台灣人受高等教育的政策。進一步說明源由之前,覺得有必要介紹日治時代的台灣初等與中等教育體制。
日治時代台灣的初等與中等教育體制
台灣人一向注重子女的教育,所以,日人普設「公學校」,大都未曾以「奴化教育」而反抗。初等教育,台人與日人分校,但皆以義務教育的普及方式執行。日人學校稱為「尋常小學校」,雖然以教育日人為目的,有少數家庭情況良好的台灣兒童亦可入學。台人入學的學校稱為「公學校」,而日人入學公學校者可以說絕無。初等學校男女不分校,低年級班男女不分班,高年級分班為原則,但是在偏辟地方設的「分校」因學童少,在一教室裡收容全校兒童,一位老師給不同學年學童輪流施教的也有。幼童教育有私立幼稚園,但是初等學校都是公立。師資方面,小學校的老師清一色是日人,公學校日籍與台籍老師都有。學童來源多的地方,小學或公學校規模大,大都設有二年制的「高等科」,給六年畢業後不升學中等學校的學生做職業訓練,或給沒有考上中學的施行補習教育。因為初等教育學校設有高等科,才有「尋常小學校」的名稱存在。
中等學校男女分校;普通中學(男校)與稱為「高等女學校」(略稱高女)的女中學之外,有師範、工、農、商、水產(以上都是男校)、家事(女校)等職業學校設置;護士與助產士大都在醫院所設訓練班培養而清一色是女生。因為在台灣,女生的高等教育學校缺如,高女的課程內容有家事、裁縫等所謂女紅之外,還有算盤簿記等商業相關技藝性學課,可在畢業之後,立即成為良妻賢母,或就職謀生,以彌補不為女生廣設職業學校的缺點。
中等學校以公立佔大多數,而公立學校的名稱以所在地名表達。但是一所有同性質學校數多則以數字區分,如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(北一中),台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等(雖然要略稱為北三高女,因為台灣有三字在上的女校無他,並且是台灣女生最多而來自全島,只說三高女全島可通)。有趣的是,台北有公立的中學四校,故皆有數字在校名上,因而容許在士林由佛教社團設立「私立台北中學校」,但是其通用的略稱是「梵中」。
一般中學與職業中等學校之外,在台北有一所特殊的中等學校。為要於1928年設置的台北帝大確保學生來源,台灣總督府設置了有四年制尋常科與三年制高等科的「台北高等學校」。尋常科接受公小學的六年畢業生,因其可直升高等科,高等科是進入帝大的「龍門」,又一年只收一班四十人而其中台灣人只有機個,可以說是台灣人最難入學的學校。
在二戰末年,為了擴大人力調用而縮短中等男校的修學年限為四年(只有一屆適用)之外,正常的男校要在學五年,女校是四年畢業,可見教育制度男女不平等是日治制度的特徵。
中高等教育的台灣人歧視
如考慮語言與生活習慣的差異,初級教育的台日生分校可以說有其合理性。但是,不分校的中等教育的執行上,有明確的台人歧視,可以我熟知的台北市為例說明。
1945年二戰結束時,台北市有台北州立中學與女高各四校,而每一校的一學年學生數約略相同,其中,二中與三高女的台灣人學生佔八到九成,其他學校的台日學生組成比率剛剛相反。所以,台北市中等學校的台日學生數比率大約一比二。但是,日人只佔全台人口的6%(600萬x0.06=36萬人),雖然大約有三成(36萬x0.3≒10萬)的在台日人居住於台北市,只佔市總人口約50萬的兩成,就可以算出台北市民台人就讀公立中學的機會,只有日人的八分之一。假如考慮台北州民亦多以台北市的州立中學為就學對象,又考慮「越區就讀」的有不少,此一比數會更低,可見台灣人進入公立中等學校的門檻之高,絕對是政策性歧視而不是台灣人天斌或進學意願不如日人。進入中等學校的門檻高,當然受高等教育的門檻更高。並且,殖民地的被統治者以醫業為最穩定的行業,所以,在殖民地台灣,受過高等教育的最大族群是開業醫。限制受高等教育機會才是奴化教育的本質所在,其基本想法與二二八事件中,很多無辜台灣精英被刺殺相同。
以下以個人的際遇,說明當年進學中學的不容易,以及日人老師對個人的溫情,以表達對日本的觀感,必要公私分開。
筆者入學北四中的經過
筆者一生經過四次入學考試,而三次集中在1941年的3到4月的該年中學入學考試期;第四次是1945年三月初投考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理科乙類;該科是以入學帝大的生醫與化學為目標的預備班。
筆者畢業於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焿子寮九份公學校;五與六年級的班導老師是剛從日本長野縣到任的「小幡晃」(Obata Akira)先生(先生是日語對老師的尊稱)。筆者的中學入學考試,小幡先生做一切安排。他叫筆者先考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,因為該校的考期最早,但是對台灣人的門檻特別高;以日語只得聽不能講的一礦夫(雖然是小戶包工自營的金礦開採業)的兒子來說,希望很低,故叫筆者以暖身態度應付即可;雖然自認是考得最好的一次,但是也如預期落榜。不過,四年後高等科考試的口試時,有一位考官問我「四年前考過尋常科吧」,讓我懷疑也許有過讓他留住記憶的事發生過。
第二應考校,是台北所有三個州立中學中,唯一以台灣人為學生軀幹(八成五)的北二中,也是大哥就讀的學校。考試前,大哥告訴筆者說,算數要得滿分,因為校長於早會中宣布,假如不是改姓名為日本式,或具有「國語家庭」的認定者(亦即接受「皇民化」程度高),算數如不得滿分就不會上榜。由於校長的固持性格,所講應該不是空話。所以,走出考場就發現算術答錯五分的一題時,大哥說趕快開始準備明年的入學考試吧一類的話。
筆者還在為了連續落榜非常不快樂的時候,小幡先生傳話,叫筆者到校見他。不知道他是在報刊或政府公報知道台北州將要新設「北四中」而開始接受報名的信息,立刻替筆者報名,到校見他當天,當面交給編號25的准考證。因為是那一年的最後一次公立中學的入學考,對一百五十的名額,有超過一千五百的報名來自全島,而以准考證號碼依序排名的榜單上,筆者名列榜頭。
假如以單純數據來看競爭率,北四中的十比一是公立中學的破紀錄高;假如考慮北四中限制台灣學生數為大約一成半的「非北二中」式,日人絕對優先入學的北一中與北三中型中學的話,筆者被錄取是很大的幸運。
小幡先生于我在北四中修完一年時,調職於台北市,就任太平公學校的「教頭」。因北四中是新設校,校舍借用北一中創校時舊木造二樓房校舍,當然不會有學生宿舍。他體念從汐止的親朋家,搭火車通學台北的辛苦,叫筆者搬進教頭宿舍玄關邊的「四帖半」,到他被日軍調用到海南島管理一家糖廠為止的一年間,讓筆者在小幡先生家,獲得「日本家庭」生活的體驗。小幡家有二男三女,最大的長女小我一歲;我的待遇完全是小幡家大哥,洗澡次序是老師之後的第二,師母最後,她也替我洗衣服,晚餐一定全家一起吃等,很奇特而難忘,有機會將以另文回憶。
「拖車夫」學校
北四中創校校長志波俊夫(Shiba Tosio)先生,很重視學生的體力與耐力磨練。在他的想法中,好像注重少數團體合作與磨練技術的「球類運動」不重要,因而棒球、籃球、橄欖球、足球之類,連校隊的成立都沒有,更不會成為體育課的運動項目。所謂「陸上競技」(track and field)與游泳是「體育課」項目,加上傳統必修的「武道課」(可選劍道或柔道)成為課程表中唯二體育相關正課。除了正課之外,亦有不少體育相關活動,介紹於下。
因是新創校關係,延期一個月而於五月一日入學之後,體育時間全用在游泳訓練,並在短縮為一個月的暑假中,在金山(舊稱金包里)的青年訓練中心舉辦一星期的「海洋訓練」,而結訓前一天舉行全生五公里游泳。記得,在岸上距三公里立兩紅旗,從一旗往外海游出一公里,轉90度沿岸游三公里,又轉90度以第二支紅旗為目標回岸。三班學生全數依照早會排隊方式,老師分岸邊觀測及隨隊看護大划船兩團,執行指揮與領隊工作;全生沒有中途放棄,達岸時都爬著沙灘離水。
假如不下雨,每星期五下午四點鐘開始,舉行全校的兩公里「記時」「鍛鍊足」,也就是校外賽跑;秋天有來回於樺山小學(現在的警政署)大門前與松山火車站的12公里賽跑。
一學年三學期,每學期舉辦一次週末的三十到五十公里「行軍」訓練,又有「一百公里行軍」;大概因於1941年12月太平洋大戰爆發,大型計畫舉辦不易,只有一次經驗。其活動內容是,中午由台大醫院邊的「台北新公園」列隊出發,在新莊開始自由行動,往南走「縱貫道路」,完成以個人體力可於24小時內的路程。筆者是在第二天的上午六點鐘到達新竹高女,用18小時走完80公里,但是,有幾個同學走到銅鑼與苗栗,超越一百公里目標。
用人力拖拉的二輪車是日治時代在台北街上常見的短程交通工具,而車伕一定跑步拉車。唯一成立的校隊,只有參加全島中學運動會的「跑步賽」,從成校的第一年就參加,獲得相當不錯的名次,於是,拖車夫學校的名聲遠播。
這等體育相關活動之外,二年級暑假於新化馬場舉行的「乘馬訓練」,三年級學期中在圓山汽車行駛考場舉辦(輪流上課)的汽車駕駛訓練(筆者雖然筆考與路考都及格,因年齡不足未得發照)等,都是難忘的技能訓練。
現在回想起來,為了各項活動的舉行,校方的籌備與管理都化很多功夫,又不會有超越體能的要求,所以,每次都圓滿結束,沒有發生過意外,而筆者獲得幾乎走遍台北盆地每一角落的美好記憶,以及游泳與走長路的能耐。
假如我們的「兵役」是學校教育的延伸
筆者受過日治時代中學的「軍事教練課」,除了一般操練與一般軍事技術(如口頭地形與環境描述、槍枝等武器的認知與保養、步槍準星校正等)之外,還有指揮「分隊(班)戰鬥」的能力考驗,都由退役的資深「配屬將校(軍官)」擔任教官。雖然筆者在中學期間,台灣人還沒有服兵役的義務,日本人學生以中學畢業或在學學歷,經過考選可得士官資格。我國的學校軍訓,在中高等學校有否士官與軍官預備教育的內容與程度,並且學校畢業後的軍事訓練,有否教育的延續作法與精神?
兵役是國家權力強制於人民的義務;以人民的立場來說,假如履行義務而對社會的安全與秩序的改進有所貢獻,又對自我的知能與體能有所提升,相信才有意義,也可以永續。
軍人必要效忠於國家,而個人必要受到上級命令的節制,才能構成有規律的軍隊。作戰的規劃上,軍兵是「可消耗」的一種「作戰資源」,與一般行業不同。是否因為軍隊戰時特有的「視人命」為可消費(expendable)資源的原則,在平常時被誤用?報載,最近十年內,軍中發生了一千三百多位士兵死亡,令人嘆息。在制度上,設有多關卡「核定」與「申訴」,顯示弊病的存在早就知道,但是,濫權事件如洪案還是會發生,表示制度之設計與執行之間有一段距離。另一方面,軍階差一級即能行使軍權於下級,而階級近者相處機會多,產生磨擦的機會也多,因而產生惡用權力的腐敗行為也有可能會增加。
透過洪案也可以看出現在的國軍軍律鬆散及行政管理的矛盾。為治安之維護,監視器的設置普遍。洪君被禁閉之處,有多達十多支的監視器,但是沒有一支的運作正常,而不正常運作也缺如管理員的紀錄。不可相信的是,不正常的理由是其電源供應插座,常被轉用為手機的充電之用。洪君被禁閉的理由是攜帶有照相功能的手機,但是,要市購沒有照相功能手機,依據筆者的體驗,最近幾年已經是不可能的事。
醫生、教師等職業,都必要有法定資格;如執行專業有失誤,必要負起責任。由報刊知道,軍隊的「禁閉」處罰,除了禁閉兩字代表的失去行動自由之外還有「體罰」,但是,執行體罰的「上官」,有否受過相關訓練而獲得執照?洪案中被起訴的執行體罰者,是受命而執行的。授命人對於受命人的能力與資格應該有所了解。然而,因執行不當而發生命案時,最大責任由受命人扛,似乎有背常理。
筆者有當過日本兵半年與台灣兵五十天的經驗。前者是二戰末期,日本台灣軍為對應美軍的可能攻台,強徵中學三年級肄業以上男生,加上男老師為臨時補充兵。筆者在學於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一年級,被編在一個重機槍連到終戰。其中最後一個月在板橋野戰醫院受惡性瘧疾的治療,撿回一命,但是因藥害而聽力受損。第二次是滿四十歲直前,在政府之「反攻大陸」設想之下,為要擔任接管大陸學術與科技單位的業務,被徵集在政戰學校受訓「接管業務」五十天,期滿被任命政戰少尉。
這等經驗,第一次是十七歲未滿,台灣軍徵用少年兵的合法性,戰後有日人提出來檢討;被徵集後,經過短暫的機槍訓練就赴守備陣地,任務是碉堡、戰壕、機場跑道的建構等工作,相處的幾全是同學與老師。第二次的五十天召集,相處的都是將近四十歲的大專老師與工程師,只上課堂課,大家所受軍事管理也很客氣,所以,兩次都沒有經驗到「老兵欺負小兵」的洪下士待遇。
雖然如此,被強迫中斷學業去當苦力甚至於炮灰,或放棄教書研究,去聽不可實現的夢話都十分不願,但是,違背軍命立刻被套上「叛國」大罪,誰敢犯?軍隊的可怕台日都有相同處,是十六歲或四十歲都有過一樣的感受。
二戰美軍沒有登陸台灣,但是空襲相當頻繁,全島的公共衛生設施被破壞不少,因而瘧疾與登革熱等蚊媒疾病猖獗,光復後還拖了一陣子才平息。筆者的北四中同屆同學有二位因瘧疾,有一位因登革熱而去世,可見這等李鴻章提到的「瘴癘」,環境一破壞立刻就呈現。戰爭會帶來破壞與不幸,因而一般民眾喜歡和平是常理。筆者是一個普通平民,年紀又大到留住祖傳的、靠自備槍砲抗爭土匪及原住民「出草」的「不和平」時代記憶,以及體驗過劉永福帶領的抗日戰爭因他離台而終止之後,日本人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是一段相當長的和平時代的事實,因而有將現實與政治觀念分開觀察與思考的習慣。
結語:台灣老人可做的社會服務
教育的執行以語言為工具。日本人設計的殖民地教育,使用日語為工具,相信是當年的台灣人不能不接受的。筆者的年齡層,母語是台灣話或客家話,學校教育使用日語,光復後改以北京官話為國語。光復時筆者就讀的台北高等學校,授課的大都是留用的日本人教授,國語教授根本找不到,所以,筆者的國語是在補習班學習一個月的注音符號使用法,以後靠字典學習發音;中文的閱讀與書寫以在中學向日本老師學到的「漢文」為基礎,自我用功學習白話文的讀與寫。所以,筆者一輩的一生中,在語言適應上所用精力與時間多。另一方面,在正規學校受教育使用日文長達十年以上,難免有許多日本文化的印記留在人格與思想中。
因為基本教育以日文為工具語言,其後學習的英文、德文、拉丁文與國語都是以日文為學習的媒介。唯一以英文為學習媒介的有法文,因為是應付博士資格考試而在留美期間上課學習的。所謂「泰西名著」都是在公學校高年級與中學期以日文翻譯書閱讀的,而日文名著亦多有所讀。這樣的學習背景,不代表筆者心醉於日本文化,而是時代背景所使然,也必然日文成為最拿手的語言。
很遺憾的是唸過的中文古典名著,只有中學的漢文課所教的論語、大學、孟子的片段與赤壁賦、正氣歌等,雖然於大學暑假期唸了三國演議、紅樓夢、水滸傳、儒林外史等小說通卷及史記的一部份,對於中國文史未下過功夫,但是相信對於中華文化的中心思想有「一般」程度的瞭解,而對於日本領台的實質利益有比較現實看法,所依據的是家訓忠恕理念。
人活於世則必要放眼於世,並且有所回饋於社會才有意義。現代傳播技術發達,有許多電子媒體可利用。現下筆者利用PC可使用自如的語言有國、英、日語三種,而透過電子媒體搜集並分析生物科學與技術相關資料的能力還有。
PC之外,衛星電視與紙本媒體也是新知的來源。筆者於漢城奧運當年,台灣開放私設衛星天線之時開始,設置一套接受日本衛星電視的天線於屋頂。近年因不能上屋頂保養天線而委人拆除,以免颱風時被吹下傷人毀物。現在雖然靠天線的免費電視廣播收不到,卻有基地放在大陸的賣日本電視收視權的公司,透過PC可收到三十七台日本電視廣播。所以,靠耳機與使用大螢幕收看日本電視台的管道還有。
至於印刷媒體,1999年退修以後,學術專刊的閱讀與利用不再,而訂閱的外文月刊與週刊縮少到各兩件。最近自覺年進力退,明年開始要再減少為各一件;將要留下的是日文月刊文藝春秋與英文週刊The Economist,而中文媒體只訂閱日刊報紙一份。雖然搜集新資料的範圍與強度已逐漸降低,利用日英文搜集科技新知的能力還有,將其透過「科技報導」一類刊物傳播於世,是老殘唯一回報養我一生台灣之道。
2013年7月陸續發生的事件,性質相當類似而引起不少思考與回憶,因而隨興寫出本篇雜文;其本意是想表達,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會因環境而變遷,而必要以時間軸統合才能形成可接受的歷史觀。(2013/08/09完稿)
2013年7月的台灣: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與台灣意識
9 August 2013